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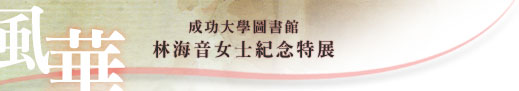

閱讀林海音:林先生的編輯、寫作生涯與台灣文壇
應鳳凰
林海音是在台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,除了她的作品,還有編輯事業,不論是編輯副刊、雜誌或主持出版社都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部分。比較新的文學史觀念不僅研究文本,也研究台灣文壇的生態及整個文學的狀況,所以我的題目「閱讀林海音」,不只討論林海音的作品,也認識林海音與整個台灣文壇關係。
三個編輯檯
首先要談的是她的編輯事業,這部分可以從她的三個編輯檯來看,第一個編輯檯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在聯合報副刊,她寫過一篇文章「流水十年間」,就是她擔任聯副編輯十年的回憶。我們知道戰後五○年代的國家文藝政策,對文壇掌控比較厲害,而林海音就是在這個時代主編「聯合副刊」。她對聯合副刊最大的改變是由比較綜藝的性質,慢慢走向純文藝,這是她對台灣文壇發展第一個的重要影響。第二,她非常重視文學,她完全以文學的好壞作為取捨的標準。她知道很多台灣本土作家,經歷了日本五十年的統治,語言上較為吃虧,當看到一些字句有很明顯的日本味道,或字句比較不通順,會一個字一個字改好了才刊登出來,她鼓勵了許多作家,這對整個台灣的本土文壇有很大的影響。其次林海音看到一篇很不錯的作品,即使作者不是一個很有名的人,她也會刊登。很多作家如林懷民、七等生、黃春明、鄭清文…的第一篇作品都是在聯副發表的。
其次,她在五○年末、六○年初她也兼任《文星雜誌》編輯,大家都知道《文星雜誌》是最受知識分子重視的刊物。文星的創刊詞--「不按牌理出牌」,就是出自何凡先生的手筆,夫妻倆聯合編輯文星雜誌,特別將西方的文學觀念和一些較新的東西編在文星中,對台灣文化的社群有相當的影響。
船長事件
五○年代是個政治力影響很大的時代,一九六三年四月的船長事件,若不是《林海音傳》記載,我們便無從知道裡面的內情。我曾聽過林海音先生提到,她常發完稿子回到家裡還會緊張,不知今天的稿件是否有問題,黃春明年輕時是一個相當叛逆的人,像她發黃春明的稿子就常膽顫心驚。現在我們來說船長事件,那天副刊版面正好空了一個位置,林先生就登了一首詩叫做「故事」,隔天總統府就撥電話給聯合報說這首詩有問題,其實這首詩只有十四行,作者叫做風遲,有人則認為這兩個字正是諷剌的諧音,並且內容影射污辱到元首。這首詩的內容是:
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
因為他的無知,以致於迷航海上
船隻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
歲月幽幽,一去就是十年的時光
他在島上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富孀
由於她的嫵媚和謊言,致使他迷惘
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,人更壯,然後啟航
而年復一年,所得到的只是免於飢餓的口糧
她曾經表示要與他結成同命鴛鴦
並給他大量的珍珠瑪瑙和寶藏
而他的鬚髮已白,水手老去
他卻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他自己的故鄉
可惜這故事是如此的殘缺不全
以致我無法告訴你那以後的情況
十四行詩的內容就是如此,結果林海音丟了聯副編輯的工作,而作者也被關了三年多,從這事件便可知道當時是的文壇處境,並造成大家的恐慌。接續林先生的主編駱學良先生曾說:「還好林先生是台灣人,又是一位女性,一向非常純潔,那首詩若是由我刊登,一定會關進牢裡。」因為林海音明快的處理,所以非常幸運僅僅掉了一個職業。但我們研究文學的人來看,這樣一個政治權利運作已深深影響台灣文學,包括文壇的發展、文風的改變,並使其他編輯人更謹慎保守。
純文學時代
一九六七年林海音創辦《純文學月刊》,她認為當時沒有一份較為嚴肅且有水準的刊物,明知辦文學雜誌會賠錢她卻做了,從一九六七年起一共出版了大約六十五期。她並在純文學月刊出刊的第二年便成立純文學出版社,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九五年一共經營了二十六年之久。純文學出版社對於六○年、七○年代台灣文學的出版有很大的影響,林先生把純文學出版社經營的非常好,特別是帶動整個文學出版。林先生可以稱為女強人,她不只經營很好的出版事業,寫了許多好的作品,更經營了一個很標準的幸福家庭,她幾乎每一方面都兼顧到,她的能力真的很強。
閱讀林海音
接下來要談林先生作品。我們知道她所有的出版事業和寫作,都是到了台灣才開始,北京栽培了林海音,而台灣成就了林海音。一九五五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冬青樹》是家的文學,筆風讓人感覺她是個非常開朗、快樂的家庭主婦,比如她提到颱風天或下雨天地上積水,孩子興奮得跑出去玩水,林海音的媽媽指責她不好好管小孩,但林海音卻覺得小孩子就應該如此,而她自己也很想加入呢!她呈現了戰後生活的面貌,雖然當時物質條件很差,卻很有家的感覺,從文學史的研究角度,那時的寫作內容非常狹窄,老是寫一些身邊瑣事,可是我們卻可以了解戰後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,如何在台灣開始生活,如何適應跟原來生長背景截然不同的環境。
城南舊事
小說《城南舊事》,也是她的經典名著。這一本書在台灣文學史上很重要,大陸也認為它是一部很重要的台灣作家作品。她生長在北京,她寫北京怎麼會是台灣文學?作為台灣文學為什麼她那麼重要?很多人把它列為懷鄉作品,甚至列為代表作。北京城,透過一個外來的小女孩英子,以小孩子的眼光來看北京,比北京更北京,至今北京人很可能還沒辦法呈現出這樣道地的北京的民俗、風光。林海音先生擁有很細膩很敏銳的眼光,特別的是,她從一個女性的角度,來看當時比較低階層一些北京人的生活,其實它的經典性也不止限制在台灣,也是中國乃至世界更大環境下的一部很好的作品,因為它呈現了真實的人性。
城南舊事不論從那個角度閱讀都是很好的作品,有人說它是女性作品,因為裡面的主角,比如惠安館裡面的秀珍、宋媽,都是以女性為主角,特別整個小說的敘述者敘述的人英子,她還沒有受過社會的薰染,用一個純潔的眼光看這世界,她即使看到一個小偷,也不會有那種我們既定的眼光,直接判定小偷是壞人。有人認為它是一部成長小說,每段故事的最後都是別離,最後一段「爸爸的花兒落了」,寫道爸爸去世了,英子也長大了。整部小說是一個成長的過程,可以是青少年成長小說,也可以是兒童讀物,或是成年讀者的對童年的回憶,它是有很多面向,我想這是經典小說很重要的條件。
以同情之筆寫女性
林海音可能是戰後台灣文學,最早擁有女性意識的作家,一直到六○、七○年代以後的女性小說的成就,其女性意識要超越林海音其實還很不容易。林海音寫《婚姻的故事》時是一九六三年,《燭芯》是一九六五年的重要作品,它們背景是五四,就是比她早的那一代,可能她母親、婆婆那一代的封建壓抑之下的女性,你可以看到她在為她們講話,這就是林海音。她曾說自己受過五四的洗禮,她已經是跳過來了,是比較新的一代,可是她看到許多在傳統之下,被壓抑受痛苦的女性。比如說她寫一位女性自小指腹為婚,她嫁過去不到兩天丈夫就去世了,明知道嫁過去馬上就守寡,還是得嫁過去,我們試想這樣女人的一生;林海音的筆也關注到女性的情慾發展,就是她壓抑這麼多年,她有一個很漂亮或者很健康的小叔,那種想像或對男性的嚮往,整個掙扎的心路歷程都寫出來,非常的動人。又如姨太太在舊時代裡種種不公平的處境…等,《婚姻的故事》大都是女性在中國傳統建制度之下,如何被壓抑的故事,這也是為何她的作品到現在都還會被提起的原因。
一九六五年她訪問美國四個月,她是戰後第一個受到美國國務院邀請的女作家,她訪問兒童文學家,文學家像賽珍珠..等,她完全走了一圈,帶了很多幻燈片回到台灣,並寫下《做客美國》。再來是《兩地》,所謂兩地大家知道是台北跟北京,她人雖然在台北但經常想起北京的童年,她一直有個願望,希望有一天可以早上從台北出發,晚上就到了北京,在九○年代她願望實現了。那個年代,兩地一直是她魂牽夢縈的,所以她散文裡常寫到這二個地方。《孟珠的旅程》是以台灣為背景,寫一個歌女的一生的故事。《窗》是何凡與林海音兩人合作的散文集,大概是在重慶南路的時候寫的。《芸窗夜讀》裡有很多她為新書所寫的序和一些讀書的紀錄,剛才所提到「流水十年間」的文章就收錄在裡面。
文壇推手
林海音很喜歡拍照,擁有好幾十本文友的照片,她曾在聯合報副刊寫過專欄《剪影話文壇》,回憶她與五○或六○年代作家及文壇的關係。八○年代的副刊影響力很大,銷量是百萬份的,讀者每天可看一篇林海音非常漂亮的跟其他文人的照片,可以感受到什麼是文人的生活、什麼是純文學、什麼是作家、這正是最好的文學教育。林海音常常給我們一個形象,一個很漂亮的女作家,一個積極而且樂於幫助別人,非常有正義感的女作家,許多文學青年在她的教育之下一路走來,對文壇越來越有認同感。
林海音與作家的互動關係非常好,在《林海音傳》有一章「林海音的家就是半個文壇」,林先生常約文友到她家吃飯,大家有事就約在那兒碰面,譬如說白先勇來了,或是張系國來了,大家都會到林先生家,本來是約三、四個人,一到場就會變成八個或十幾個,大家都來了,朋友又帶朋友來。她為台灣文壇創造一個文藝社群的印象,她無意間給台灣民眾創造的一個具體,就叫「文壇」的東西。在七○、八○年代特別是八○年代末,我們都知道台灣有個文壇,林先生她開的出版社,辦的雜誌就叫做純文學,她常常講純文學,所以民眾越來越清楚什麼叫純文學,純文學跟大眾文學、跟商業的文學就自然而然的分開了,文壇也就越來越成熟,文學作品越來越有文學的自主性,也就是文學第一,商業性,或是政治正確性越來越不重要。林先生在文壇所扮演的,是一個很正面的角色,所以我們說林先生有一雙推動文壇發展的手。(丁櫻樺紀錄整理)
作者簡介
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系文學博士。任職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,教授台灣女性文學與理論專題、戰後臺灣文學史料專題等課程。二十餘年來不斷致力於編纂、書目,整理文學史料之工作,此外也寫小說、散文和書評。